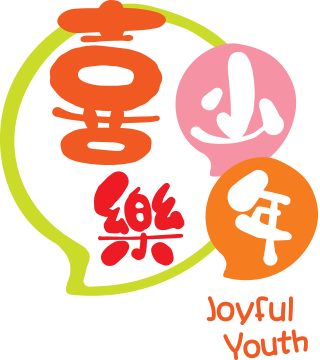昔日文章


綠滿窗前
2014.02.23
從「青年」一詞談起
有人問我,最近政府施政報告有用「年青」一詞,而有人說應用「年輕」才對,究竟「年青」一詞是否可用?
我的看法是,詞語是會不斷滋生的, 倘多人接受了(或者說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則不能忽視它的存在,而編詞書的人也應考慮把它們收錄。
例如「姿采」,這是一個典型的香港詞。曾經有相熟的老師對我說,很多學生在作文中把「多姿多采」寫成「多姿采」。初時當然不能接受,要他們更正。後來連「多」字也闕如,變為「姿采」。「姿采」、「姿采」⋯⋯出現次數多了, 也只好無奈的接受。現在「姿采」一詞, 雖然一般詞典還未收錄,但報章雜誌隨處可見,在香港顯然已生了根,你能說它不規範嗎?
又例如「關愛」一詞。記得二十多年前,因工作關係,經常到學校探訪,向學校提供教學意見。有一次,到學校查看學生的作文簿時,發現學生文章中出現有「關愛」一詞,但被老師刪去,被改為「關心」。那老師年近六十,是一位資深教師。那年代,以我所知,「關愛」一詞在台灣流行,在香港則較少人用。老師不接受,我想,大概由於在當時還未夠規範吧。至於「跟進」、「反思」、「願景」、「解讀」等等詞彙,也是這三十年內才出現的,現在已被廣泛應用了,即使有些詞書仍未收錄,但誰敢說這些詞不規範呢?
「年青」一詞,目前不論在口語或書面語,都是一個常用詞了。詞書未收,只是編詞書者失職而已。


種子的力量
2014.02.23
關愛孩童育人靈 道明會與基督學校修士會
編撰:保祿女兒 插圖:穆家易
顧問: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朱益宜教授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若望福音12:24)
關愛孩童育人靈
道明會與基督學校修士會
源於西班牙的道明會早於十六世紀已有會士到中國傳教,並成立聖母玫瑰會省。修會在香港的歷史則可追溯至1861年,會省把總部從澳門遷往香港,七月一日,新的修道院在堅道正式啟幕。香港開埠初期,不少澳門商家遷到香港,外籍人口也不斷增加,加上香港的港口角色日漸重要,帶來莫大的福傳機遇。
為培訓修士,羅福范士豪神父(Fr. Francisco Noval)得到政府和教會批准後,在粉嶺買了一幅土地打算興建新修道院,這項計劃卻因政治原因而擱置。1935年,修會終於在跑馬地玫瑰崗建立聖大亞伯爾修院,負責培訓來自世界各地在遠東傳教的會士。
上世紀五十年代,鑒於中國內地局勢不穩,該會決定在政治形勢較為穩定的菲律賓,成立新的神學院。道明會會士遵循會祖聖道明(St. Dominic)的方向,教育和福傳是他們使徒工作的重心。聖大亞爾伯修院不再擔任培訓會士的角色,更在1959年改為玫瑰崗學校,教導香港新一代認識基督的真理,培育青年認識福音和人的價值。
1875年,在高主教(Bp. Timoleone Raimondi, 1827-94)的邀請下,六位基督學校修士會修士來港辦學。這個由聖若翰.喇沙(S t. John Baptist de La Salle)所創立的修會亦稱為喇沙會,修會的修士們不會擔任其他教會事務,全心致志地投入教育工作,將一生奉獻於教育孩童,讓孩童認識、敬愛天主。修士們矢發終身聖願(終身修士),不會成為神父 。
抵港後,修士們接收了位於堅道的一所校舍,將該校改名為聖若瑟書院,成為全港第一所天主教男子學校,由Hidulphe-Marie Nicholas修士(1835-86)出任校長。聖若瑟書院收錄的學生,不分貧富。起初, 學生人數只有數十人,並以葡籍學生為主。隨著不少葡國人由澳門移居香港,加上學校於1878年開始收錄中國學生,教授他們英語會話及書信,學生數目倍增,校舍不敷使用。聖若瑟書院遂於1881年搬遷至己連拿利的校舍。
鑒於住在九龍區的學生每天都要長途跋涉、乘渡海小輪上學,當時的校長艾瑪修士(Br. Aimare Sauron, 1873-1945)於1917年在尖沙咀漆咸道,創立聖若瑟書院分校(今喇沙書院前身)。1918年發生一場地震,令己連拿利校舍嚴重損毀,於是艾瑪修士購下學校位於堅尼地道的現址(當時為舊德國會所),繼續教育工作。
學校根據辦學團體的理念運作發展,各校校徽正正形象化地表達辦學的宗旨和方向。
聖若瑟書院
聖若瑟書院校徽上方的十字架和中央的五角星,分別清楚地表明這是一所信仰基督的基督學校修士會學校。左方的書本和燈代表知識和學習的明燈,右方由三個倒「v」組成的圖案則代表勇氣和堅毅。該校校訓「勞動與美德」(Labore et Virtute)亦是校徽的重要部份。
玫瑰崗學校
玫瑰崗學校的校徽上方是一顆八角星,代表天主的光。中央是黑白色相間的十字架, 黑色代表犧牲,白色代表純潔。校徽下方亦標明了學校的校訓「真理」(Veritas)。整個校徽的意思是天主的真光帶領學生,走正確的道路。


童書的旋律
2014.01.12
《看不見》的世界是怎樣的?
今年的學生對我兒時的玩意特別有興趣, 我當然樂意為他們介紹兒時的遊戲, 像「狐狸先生幾多點」、「一,二,三紅綠燈」、「大風吹」⋯⋯但我最愛玩的是「耍盲雞」(摸瞎子)。其實「耍盲雞」跟躲貓貓的玩法差不多,只是做「鬼」的要蒙著雙眼,單靠聽覺來抓人。當「鬼」的,不但要留心周圍的聲音,也要牢記周圍的環境,這樣才不會被絆倒或撞傷。我們很愛玩這個刺激又有趣的遊戲,因為我們都知道它只是個遊戲—— 摘下蒙眼布後,便可以重見光明。不過,失明人士就永遠沒有摘下蒙眼布的可能,他們一生都要活在看不見的世界裡。要了解盲人的世界,我們不能抱著像玩「耍盲雞」般的「遊戲」心態,而是通過模擬的體驗活動,真切地感受、體會失明人士無日無之的恐懼與壓力。
台灣畫家蔡兆倫的作品《看不見》,寫的就是這麼一個故事。他讓讀者通過閱讀與模擬的體驗活動,體會「看不見」的恐懼與焦慮,使讀者從而明白身邊有著「看不見」的一群,他們需要關愛,需要尊重。要一個孩子從家裡走到常去的公園,那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當他被蒙著雙眼, 一切便變得複雜和困難。首先,從家出發,他要知道怎樣出門,家中一切必須瞭如指掌。走出家門後,他必須要知道每層樓之間有多少級階梯,逐級而下,這樣才能安然走到街上。最後走到街上了,危險正式開始,因為街道上的一切都是不可預測,他不知道自己會遇到甚麼,碰上甚麼。人類普遍對看不見,不清楚的東西都會感到恐懼。於是,畫家便運用了張開口、準備吃人的恐龍,強化了看不見的情況下過馬路的危險;以傾斜的迷宮,重複拼貼男孩的影像,表達了對前路不確定的恐懼。無論是多熟悉的路,因為看不見的緣故,我們很容易喪失距離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遠,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只一點點的不確定,那恐懼、惶恐會變得無限大。
不少一般人認為易如反掌的事情,對失明人士來說,都是挾山超海的困難。如果我們能體驗他們的困境,在有機會幫助他們的時候,便能清楚地明白他們的需要,了解他們的感受。我們並不是要高高在上的可憐他們,而是明白失明人士跟我們一樣,需要別人的關心,需要別人的尊重。《看不見》的書末提供了一份小冊子,教導我們協助盲人的基本方法,只要我們多用心思學習怎樣正確地與他們相處及互動,便能減輕盲人的許多不便, 也能讓他們遠離危險。
很多人誤以為兒童圖畫書必須要用上繽紛的色彩,但《看不見》全書基本只用上黑白二色,突顯失明人士所面對的黑暗,畫家也刻意不去描畫書中事物的細節,只以大色塊平塗的方式顯示事物的外形,目的在切合失明人士看不清、看不見,只知事物大致外貌的特徵。當我們的視覺被剝奪後,其他感官便會變得敏銳 —— 創作者以不同的字型,表達了從四面八方襲來不同質感的聲音;以不同的線條、符號, 及文字排列,呈現了花香、涼風、聲音以至被觸碰的感覺。於是,讀者透過畫面、文字與符碼,明白盲人是如何認識世界。全書結束前的雙跨頁是全書的亮點,創作者以彩色描繪孩子到達公園,並在除下眼罩後所見到情景。蔡兆倫在這唯一的彩色雙跨頁中,運用了豐富的色彩向讀者展示能看見的美好願望與想像:蒙娜麗莎抱著兔子坐在公園、撲克牌中的國王帶著泥耙子到來、女孩用噴罐噴出彩虹⋯⋯所有的都是奇哉偉哉!
能看見,實在是神奇美妙!
不過,當我們以為「看見」是理所當然的時候,我更期望《看不見》這本書會讓我們察覺,身邊仍有一群失去視力,需要我們關心、尊重的人。


童書的旋律
2014.01.05
諾和我 無限小 變成 無限大
不少學校都在提倡關愛文化,希望學生能愛護身邊的人,關心他們的需要。俗語說:「送佛送到西」,即是說做好人要做到底,但怎樣才能算做到底?我想這實在難以定義,因為每一個人的底線都不一樣,不可能有劃一的標準。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想想自己能夠幫助人的底線在哪裡?幫助別人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你能跟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成為朋友嗎?而這個人早已在街頭流浪了好幾個年頭。你能無條件為他付出,甚至說服你的父母,讓他成為你家的一份子嗎?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諾和我》(No et moi)中的盧.貝爾蒂尼亞克(Lou Bertignac)卻能將這個無限小變成無限大。
盧 ── 是一位在十三歲已跳級讀高二的資優女生,雖然學業成績很好,但她最怕口頭報告。盧並非不善言辭,相反,字典裡的字,她差不多都學會,只是每跟人說話,她就沒法找到適當的詞彙,像她的說法:「語言在我要將他們說出來的那一刻,就會像枯葉一樣地散落開,找不到方向。」不過,她因為要完成一個關於年輕女遊民的口頭報告而結識了諾(No)── 十八歲的女遊民(雖然她從不承認她是遊民)。
資優女孩跟女遊民,兩人就好像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沒有交集的可能。但為了完成口頭報告,盧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跟諾溝通交流,諾亦也娓娓道來自己的生活,甚至將自己的朋友介紹予盧認識。在咖啡館裡,兩人的友誼漸漸建立起來,憑藉真心,兩人的距離愈來愈近, 兩個不同的世界慢慢匯合在一起。
看似日漸穩固的友誼,卻在盧完成口頭報告後變得不可預測:諾不見了,盧再也找不到諾。在諾失蹤的這段時間,盧發現自己並不是施予者,真正需要對方的是她。她到過所有諾會出沒的地方,並去找諾的朋友,希望能尋得諾。終於,盧在愛心餐廳找到諾,並萌生要將諾帶回家的念頭,她認為這樣做,諾便有了一個屬於她的家,能開始她的新生活。於是,盧努力遊說父母,沒想到,那位答應她的要求的,竟是患了嚴重情緒病,並因為幼女突然猝死,將自己完全隔離於其他人的母親。盧將這個無限小變成無限大。
故事到了這裡,該應是兩人幸福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吧!可惜,這並不是一個由王子和公主當主角的童話故事。諾不是一隻被遺棄在街頭的小狗,並不是給她吃和睡,給她一點愛,便能馴養她。諾是一個已流浪街頭多年的女遊民,要她融入一個陌生的家庭,是一件非常複雜困難的事。雖然她十分努力地符合盧的爸爸的要求,也跟盧的媽媽相處得很好,但她在流浪的期間所沾上的嗑藥惡習,最終令她被盧的爸爸驅逐出這個家。
諾曾經跟盧說過,「如果你馴養了我,你就是我的唯一了。」可惜,人並不是寵物,終歸不可能被豢養。最終,諾也離開盧,不知所蹤,再也沒有她的音訊。但這件事改變了盧,讓她一夜之間成為了大人,明白家的真正意義。作者德爾菲娜.德.維岡(Delphine de Vigan)在書中除了探討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家庭的建構外,還帶出法國遊民,尤其女性遊民所面對的問題。女性遊民在街上面對的, 不只是怎樣找食物,怎樣找一個容身之所,她們更時刻受到暴力的威脅。「當你流落在街頭的時候,你永遠都是別人嘴中的獵物」,簡單的一句,道盡了她們的辛酸。在香港,當我們遇到流浪漢的時候,父母親也許語重心長地勸誡我們:「不用心讀書,將來你就會變成他們那樣。」其實,我們可曾想過他們流落街頭的真正原因?諾說得對「她們不是遊民,不是垃圾,她們是像你『盧』一樣的普通女人。」
闔上這本書,有一個段落一直停留在我的腦袋裡。盧曾說:「人就是那麼奇怪,他們能夠毫不費力地把一隻狗帶回家,卻沒有人願意讓遊民走進自己的家門。」對於遊民,我們可以怎樣去幫他們呢?我們幫助他人的底線在哪裡?我們能將無限小變成無限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