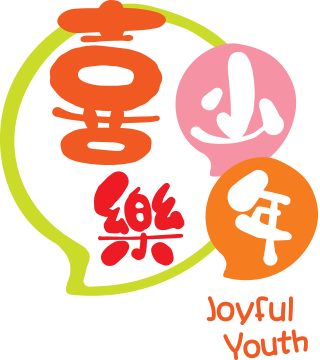昔日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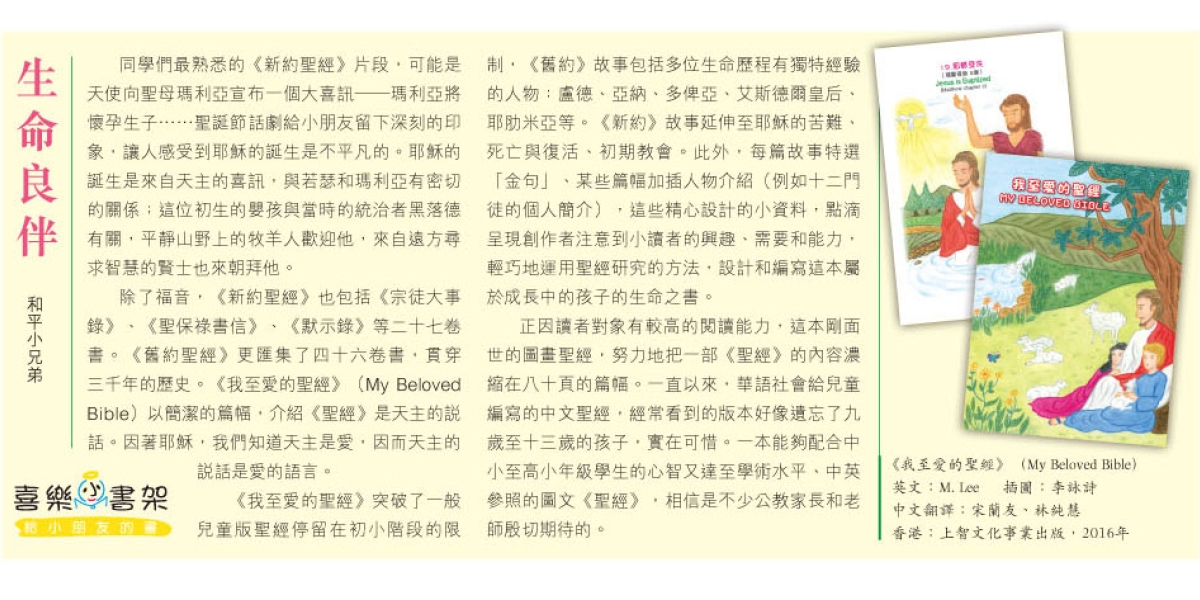

生命動力
2016.06.25
【喜樂小書架】生命良伴
同學們最熟悉的《新約聖經》片段,可能是天使向聖母瑪利亞宣布一個大喜訊——瑪利亞將懷孕生子⋯⋯聖誕節話劇給小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讓人感受到耶穌的誕生是不平凡的。耶穌的誕生是來自天主的喜訊,與若瑟和瑪利亞有密切的關係;這位初生的嬰孩與當時的統治者黑落德有關,平靜山野上的牧羊人歡迎他,來自遠方尋求智慧的賢士也來朝拜他。
除了福音,《新約聖經》也包括《宗徒大事錄》、《聖保祿書信》、《默示錄》等二十七卷書。《舊約聖經》更匯集了四十六卷書,貫穿三千年的歷史。《我至愛的聖經》(My Beloved Bible)以簡潔的篇幅,介紹《聖經》是天主的說話。因著耶穌,我們知道天主是愛,因而天主的說話是愛的語言。
《我至愛的聖經》突破了一般兒童版聖經停留在初小階段的限制,《舊約》故事包括多位生命歷程有獨特經驗的人物:盧德、亞納、多俾亞、艾斯德爾皇后、耶肋米亞等。《新約》故事延伸至耶穌的苦難、死亡與復活、初期教會。此外,每篇故事特選「金句」、某些篇幅加插人物介紹(例如十二門徒的個人簡介),這些精心設計的小資料,點滴呈現創作者注意到小讀者的興趣、需要和能力, 輕巧地運用聖經研究的方法,設計和編寫這本屬於成長中的孩子的生命之書。
正因讀者對象有較高的閱讀能力,這本剛面世的圖畫聖經,努力地把一部《聖經》的內容濃縮在八十頁的篇幅。一直以來,華語社會給兒童編寫的中文聖經,經常看到的版本好像遺忘了九歲至十三歲的孩子,實在可惜。一本能夠配合中小至高小年級學生的心智又達至學術水平、中英參照的圖文《聖經》,相信是不少公教家長和老師殷切期待的。


微風細語
2016.06.25
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
長崎位於日本九州西端,是背山面海的狹長港都。
1945年8月9日早上11點2分,一顆原子彈掉落在長崎的浦上地區,天空中開出一朵形狀駭人的蘑菇雲。「山里小學」位於距離爆心地七百公尺處,全校一千三百名學童中,僅有兩百人生還。長崎浦上化為寸草不生的焦黑荒野,許多孩子成了孤兒, 肉體慘遭輻射侵蝕,心靈破碎,傷痕累累。
四年後,永井隆博士邀請三十七個山里小學的學生,手寫或口述自己的原爆體驗。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書中最小的孩子才四歲,最大的則是十二歲。永井隆博士的目的,其實也是長崎人共同的渴望,就是讓原子荒野上稚嫩的吶喊,更廣闊、更清晰、更響亮地傳達出去:
「不要戰爭!不要戰爭!」
在原子雲陰影下掙扎求生的孩子們,默默忍受遠超過他們所能承受的苦痛。驚人的是,整本書中卻找不到任何一句抱怨或仇恨。三十七個孩子中,有人從此帶著無從遮掩的傷疤、有人失去父母或兄弟姊妹、也有人喪失家園或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固然不明白引發戰爭的仇恨糾葛,卻柔順地接受了天主的安排,沒有人問「為甚麼是我? 不公平!」,也沒有人叫囂:「總有一天要報仇!」相反的,他們讓充滿苦難的生命成為見證, 化為祈禱。
「奶奶總是對我說:『一切都出自天主的旨意。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我也想要和奶奶一樣,有一顆美麗的心。」(辻本一二夫,當時五歲)
「當時,我們的確覺得難堪,的確難以忍受……可是,那無邊無際的苦難與犧牲卻又以完全出乎預料的方式,為現在的我們帶來莫大的幸福……」(深堀正,當時八歲)
「媽媽的燒傷復原後,留下一塊巨大的傷疤。不過,我並不覺得那塊傷疤難看。」(片岡泰男,當時十歲)
本書出版後,永井隆博士按照篇幅比例,將版稅分給三十七位小作者,並邀請他們從所得中捐出一部分,共同豎立名為「那些孩子們的碑」的紀念碑。碑上沒有任何文字,只鑲了一枚銅板,以浮雕方式描繪一位跪在烈焰中合掌向天祈禱的小女孩。直到今天,山里小學的兒童們依然每年聚集在碑前, 為逝去的學長學姐祈禱,重新宣告和平誓言。
「原子彈,很惡劣,很痛,再也不要了!」
《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紀錄的並非過去的歷史,而是貫穿現在、直通未來的和平禱聲。


小學專題
2016.06.18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奇妙的生命 學生才藝晚會
生命原是個奧跡,「這是天主賦予人的無價之寶;生命在本質上就是神聖的。」
《公教學校教育願景與使命》
(本報專題)天主教總堂區學校於上月初假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辦名為「奇妙的生命學生才藝晚會」,透過舞台上的不同表演項目,讓全校每一位學生都有機會發揮才能,在人前綻放他們各自獨特的生命光彩。宗藹雯副校長是才藝晚會的統籌,她表示各人都很期待今次的演出,如今整個活動能順利進行,是全校上下辛勞合作的成果。
宗副校說:「我們用了兩週的時間讓學生準備,事前各級老師們既要因應學生的情況設計節目,又要在不影響教學的情況下安排時間讓學生去練習和綵排;我們所有的舞台布景均由校工們製作;晚會的橫額由家教會安排,另外,單是為當晚演出的學生化妝和弄頭髮,便有約四十多位來自不同級別的家長前來協助。」
每位學生都有潛能
宗副校指:當晚十三個表演項目中,全校三百四十多名學生有一半人參與當中八個專項訓練的節目,如在學界或校際賽中獲獎的英語話劇、合唱、舞龍舞獅、鋼琴獨奏或親子合奏等,其餘一半學生則在分級表演中嶄露頭角,例如一年級生結合功夫、背誦《三字經》和《唐詩》表演的〈功夫三字經〉、二年級生的舞蹈表演〈動感舞〉、三年級生以說唱形式表達的〈我愛香港〉、四至六年級生集合擊鼓、打籃球、速疊杯和體操的〈節奏匯〉。「校方每年都會舉行才藝表演,今年作了一個新嘗試,我們想傳達的訊息是並非只有所謂的精英才可以踏上舞台表演,任何一個學生都可以,只要他們有機會。」
宗副校相信每個學生都具有潛能,例如有些人天生有很強的節奏感,像在〈節奏匯〉中帶領其他學生擊鼓的五年級生Ng Shauncey Jimfred Gloria(吳福星),他是一名中菲混血兒,日常他也會在家裡敲打物件訓練節奏感,「當時在兩個大鼓旁,有其他同學隨著節奏在打籃球及玩速疊杯,我有份參與一起玩,感覺很好。」福星坦言表演後令他自信大增。自信心得以提升還來自透過自身的努力克服困難及得到所重視的人的支持。在中文話劇〈公主「假」到〉中飾演國王的五年級生Joseph Pascalis是印尼人,要日常以英語溝通的他背誦中文劇本著實有點困難,尤其有些句子頗長,對他來說更感吃力,幸好透過他的努力和老師的指導,最終他都能順利過關,身為公教生的他還表示:演出前一晚,特別為此祈禱。「感謝主,我沒有放棄,爸媽也替我高興。」在同劇中有份參演的四年級生Ezekiel Gomes,在劇中飾演多個角色,包括美術老師和皇宮神祇等,他是在港出生的印度裔人士,對他來說,念廣東話對白沒有難度。只消五分鐘,他便可記牢那五、六行的對白。「我感到最開心的是我所有的家人,包括我的代母當晚也有來看我演出,他們看過我的話劇和醒獅表演後,都來恭賀我。」Ezekiel還發現了自己有演戲的細胞,只需透過表情動作便可表達出倦透和汗流滿面的情形,令他十分享受這次的演出機會。
個人得到團體支持
個人的才能得以發揮,亦需要得到團體的支持,六年級生鄧胤澤對此深有體會,他當晚身兼多職,包括其中一位大會司儀、在〈節奏匯〉中打籃球、在〈龍獅共舞〉中舞龍尾,他每一項都應付自如。「我們在練習〈節奏匯〉時,八位打籃球的同學全部都要跟足節奏去拍球,如果其中一人跟不上,其餘各人都要一起重頭練習,直至完全沒有失誤,那份互相體諒和支持的力量很大。另外,我是在今年才加入學校的中國舞獅訓練班,我在演出前臨時被調往去舞龍尾這般重要的位置,幸好得到其他同學的提點,大家一起練習日久,像是已經心靈相通,可以互相補足。」他和其他有份參與演出的同學都覺得表演能盡顯他們的活力。
看見學生們在表演過後都有所收穫,宗副校及身兼節目經理和〈節奏匯〉負責老師的曲敏兒主任同感欣慰,宗副校還笑稱:今次的才藝晚會是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皆因有些學生原本比較內向或不願嘗試,經過老師們的不斷鼓勵,將發掘到的學生才能說出來,其他學生從旁確認,讓學生本身也看到自己的價值和長處。「生命來自天主,每個生命都是獨特、寶貴與神聖的,天主賜予每個人不同的才能,讓我們去發掘、發揮和善用,服務他人,造福社會。」牧民助理林貴芬總括分享。(敏)


生活樂章
2016.06.18
鳥
初中時期,曾讀中國語文課《貓捕雀》一文,印象深刻。
課文敍述作者薛福成看見棗林裡老貓捕殺雀母的情景。文中,雀鳥是弱小的,無助的,牠們對於老貓的殘暴行為,不但毫無反抗能力,就是雀母遇害以後,雛鳥也只能在室外啁啾徘徊。作者(人類)雖然在旁觀察,卻由於不及救援,心裡既感到難過,也對雛鳥予以同情。
可是,希治閣(Alfred Hitchcock)執導電影《鳥》(The Birds),對鳥兒的描述,與《貓捕雀》剛好相反,跟人類的關係也欠和諧。
電影故事由女主角進入一間裝飾華麗的寵物店開始。富小姐在店內邂逅男主角,並討論人類於鳥籠飼養雀鳥的問題。這時,觀眾或會期待浪漫故事的開展,只是,當富小姐帶同一對小鸚鵡到達海灣區以後,讓人驚恐的事情逐一發生;其中,不乏有暴力場面,例如:一大群黑鳥進襲學校,走避不及的孩童,被弄至血流滿面,但黑鳥沒有停止追襲行動,還繼續伸出利爪,撲向學生。
導演運用鏡頭與攝影技巧,把一幕幕雀鳥肆暴的場面,活現觀眾眼前;此外,他還透過聲音與視覺元素,營造驚悚氣氛。電影中多次出現的,是數以百計的黑鳥,或聚於高懸的電線竿上,或佇立在兒童遊樂設施之間,俯視地上行人活動;畫面一片死寂,像要預示不幸的事情快將來臨。至於人類的抵禦行動,也是有的,只是有點束手無策而已,例如:男主角把屋內所有窗戶用厚重的木條封閉,把家人置於其中;那知,當木門一處一處被刺啄,屋外又不斷傳來拍打羽翼的聲音,不待雀影出現,人類便知道危難逼在眉睫。
戲劇人物多次在電影中提問:何以雀鳥突然來襲?這或許就是觀眾感到不安之處,即人類對於大自然界生物之異常行為,或未能理解。因此,當戲劇人物面對雀鳥侵襲,或表現驚惶,或情緒失控;至電影結束,由於人類無法妥善處理雀鳥侵襲問題,只好離開美麗的海灣居所作逃避。
由此看來,雖然《貓捕雀》寫於清代,而《鳥》完成於1963年,似仍有閱讀和觀看價值,以提醒人類思考跟大自然生物之和諧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