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文章


小學專題
2016.12.10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圖騰藝術展
(本報專題)將軍澳天主教小學每年都會舉辦視覺藝術展,今年的主題是「圖騰」,意指民族、族群和當地人表達的特色,故此是次主題能讓各班學生展示他們的特性。視藝科周君瑜老師表示,現今人們普遍把圖騰當作紀念品;因此利用圖騰作主題,能讓學生學會欣賞其顏色、含義等,重新用藝術角度認識圖騰。
就讀五年級的麥嘉兒展示的圖騰作品,是五、六年級學生共同製作的,約五米高,是這次展覽中最高的製成品。「感到真的很自豪,我們先參考圖片再製作,沒想到會這樣高。」因為五、六年級的學生已經開始思考未來方向,所以跟老師商量後,決定用夢想職業作主題。同學們在作品四周畫上不同的夢想職業, 用木板固定,並用膠紙黏合。由於是天主教學校,作品頂部是一隻代表聖神的白鴿,再配合環保概念,以汽水罐作翅膀,使作品更具意義。製成後,嘉兒感到很滿意,因為做出來的效果非常棒。
六年級生劉文靜和洪丞鑌表示,製作過程十分好玩,「因為可以自由發揮, 又可以試用熱溶膠、釘槍等工具, 平時只會用到釘書機。」文靜說。丞鑌補充,鷹的翅膀經常掉下來,用普通白膠漿不夠穩固,因此要用到熱溶膠等工具。他們班所製作的圖騰,展現出學生六個年級的特性,最底層的是小花小草,代表一年級的脆弱性;二年級是代表單純的綿羊等等。這個圖騰最特別的地方,是紙碟上寫上各人的姓氏,象徵著全班每個人都參與其中。
在過程中,學生體會到分工合作, 因為如果只有一個人製作,便很難製作出整個圖騰。文靜還說:「完成作品後要匯報,還可訓練我們的口才。」雖然過程好玩,但他們也面對一些困難,例如升降機裝不到這麼大的圖騰,他們便要合力把作品從六樓搬到一樓禮堂。嘉兒也表示,班中二十七位學生一起搬動圖騰,是最困難的事情;但是「一齊創作,一齊辛苦」,整個過程帶給她很多回憶。在面對逆境時,當想到那些畫面,便能克服困難。
教導嘉兒班級的周君瑜老師( 小圖右)表示,平時學生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因為自己畫的圖畫不美麗便會感到失望。這次展覽讓學生明白,只要集合眾人的創作和參與,就會出現美麗的製成品,學生從中也獲得成功感。另一教授視藝科的勞逸韶老師(小圖左)也提到,成果美麗與否並不重要,最重要是過程中學會欣賞別人,與人合作,最後學生能做到「不分你我,是我們班的作品」。老師還會跟學生一起嘗試不同的顏料、材料,例如周老師教導學生用原支顏料, 直接塗在木板上,使質感更厚、更原始, 老師和學生都能從中一起成長和學習。(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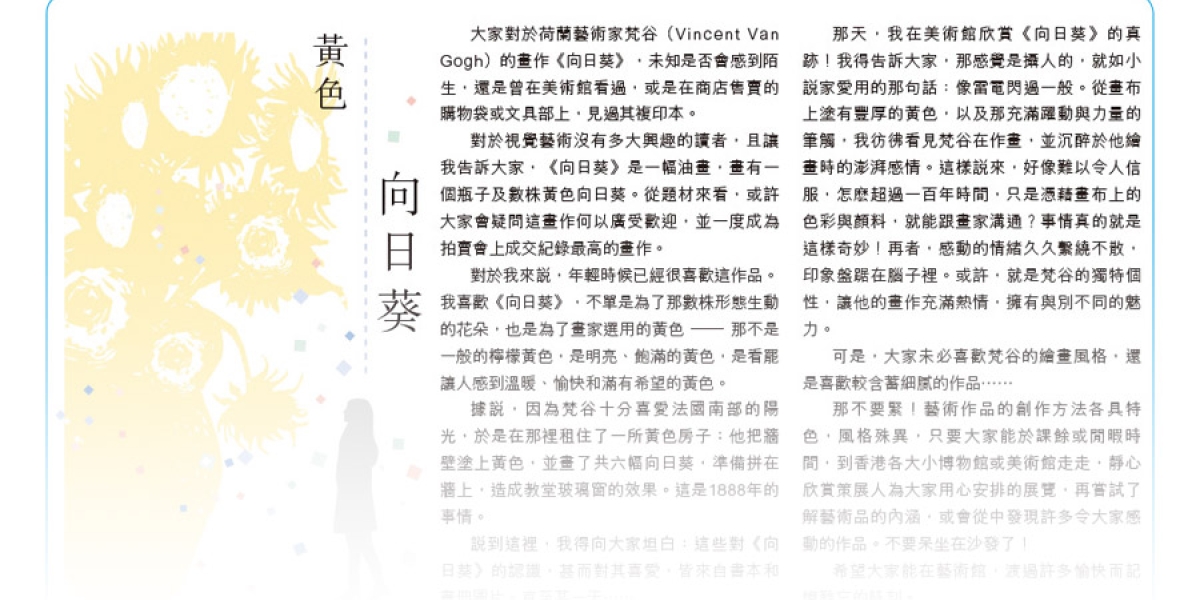

藝文知趣
2016.05.14
黃色 向日葵
大家對於荷蘭藝術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畫作《向日葵》,未知是否會感到陌生,還是曾在美術館看過,或是在商店售賣的購物袋或文具部上,見過其複印本。
對於視覺藝術沒有多大興趣的讀者,且讓我告訴大家,《向日葵》是一幅油畫,畫有一個瓶子及數株黃色向日葵。從題材來看,或許大家會疑問這畫作何以廣受歡迎,並一度成為拍賣會上成交紀錄最高的畫作。
對於我來說,年輕時候已經很喜歡這作品。我喜歡《向日葵》,不單是為了那數株形態生動的花朵,也是為了畫家選用的黃色 —— 那不是一般的檸檬黃色,是明亮、飽滿的黃色,是看罷讓人感到溫暖、愉快和滿有希望的黃色。
據說,因為梵谷十分喜愛法國南部的陽光,於是在那裡租住了一所黃色房子;他把牆壁塗上黃色,並畫了共六幅向日葵,準備拼在牆上,造成教堂玻璃窗的效果。這是1888年的事情。
說到這裡,我得向大家坦白:這些對《向日葵》的認識,甚而對其喜愛,皆來自書本和畫冊圖片。直至某一天⋯⋯
那天,我在美術館欣賞《向日葵》的真跡!我得告訴大家,那感覺是攝人的,就如小說家愛用的那句話:像雷電閃過一般。從畫布上塗有豐厚的黃色,以及那充滿躍動與力量的筆觸,我彷彿看見梵谷在作畫,並沉醉於他繪畫時的澎湃感情。這樣說來,好像難以令人信服,怎麽超過一百年時間,只是憑藉畫布上的色彩與顏料,就能跟畫家溝通?事情真的就是這樣奇妙!再者,感動的情緒久久繫繞不散,印象盤踞在腦子裡。或許,就是梵谷的獨特個性,讓他的畫作充滿熱情,擁有與別不同的魅力。
可是,大家未必喜歡梵谷的繪畫風格,還是喜歡較含蓄細膩的作品⋯⋯
那不要緊!藝術作品的創作方法各具特色,風格殊異,只要大家能於課餘或閒暇時間,到香港各大小博物館或美術館走走,靜心欣賞策展人為大家用心安排的展覽,再嘗試了解藝術品的內涵,或會從中發現許多令大家感動的作品。不要呆坐在沙發了!
希望大家能在藝術館,渡過許多愉快而記憶難忘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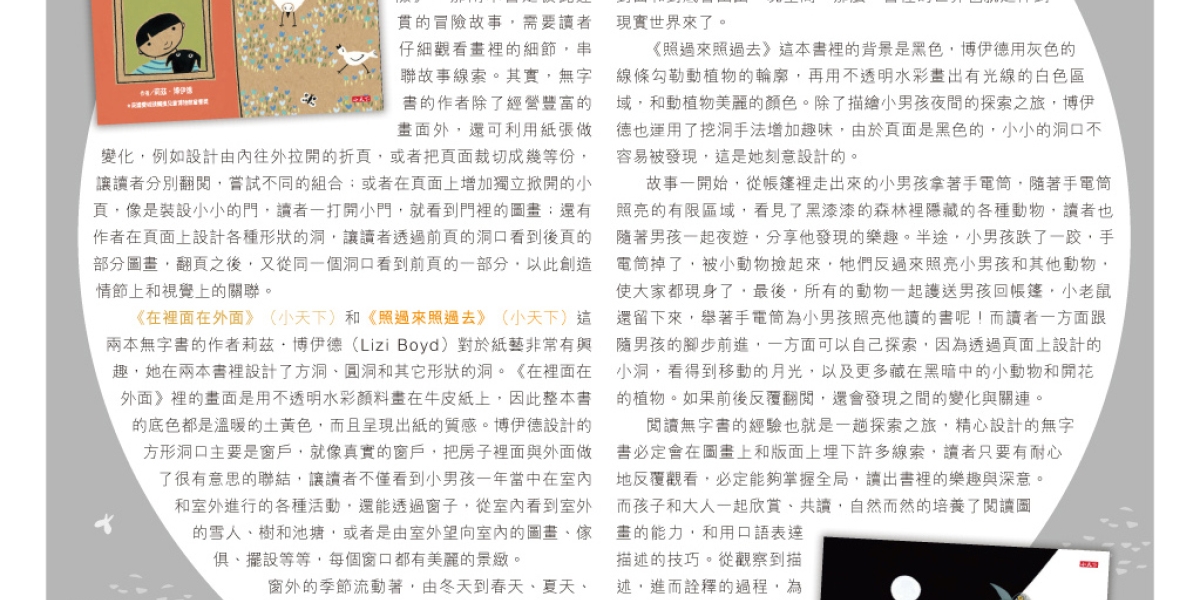

童書的旋律
2016.02.20
在頁面上挖洞的無字書——《在裡面在外面》、《照過來照過去》
上個月,我們介紹過精采的無字書《旅程》和《歷險》,那兩本書是彼此連貫的冒險故事,需要讀者仔細觀看畫裡的細節,串聯故事線索。其實,無字書的作者除了經營豐富的畫面外,還可利用紙張做變化,例如設計由內往外拉開的折頁,或者把頁面裁切成幾等份, 讓讀者分別翻閱,嘗試不同的組合;或者在頁面上增加獨立掀開的小頁,像是裝設小小的門,讀者一打開小門,就看到門裡的圖畫;還有作者在頁面上設計各種形狀的洞,讓讀者透過前頁的洞口看到後頁的部分圖畫,翻頁之後,又從同一個洞口看到前頁的一部分,以此創造情節上和視覺上的關聯。
《在裡面在外面》(小天下)和《照過來照過去》(小天下)這兩本無字書的作者莉茲.博伊德(Lizi Boyd)對於紙藝非常有興趣,她在兩本書裡設計了方洞、圓洞和其它形狀的洞。《在裡面在外面》裡的畫面是用不透明水彩顏料畫在牛皮紙上,因此整本書的底色都是溫暖的土黃色,而且呈現出紙的質感。博伊德設計的方形洞口主要是窗戶,就像真實的窗戶,把房子裡面與外面做了很有意思的聯結,讓讀者不僅看到小男孩一年當中在室內和室外進行的各種活動,還能透過窗子,從室內看到室外的雪人、樹和池塘,或者是由室外望向室內的圖畫、傢俱、擺設等等,每個窗口都有美麗的景緻。
窗外的季節流動著,由冬天到春天、夏天、秋天,再回到冬天,小男孩在不同的季節裡到室外堆雪人、放風箏、種蔬菜、玩帆船、掃落葉、滑雪橇,或是待在室內做勞作、演戲、露營⋯⋯,並且把做過的事情畫成圖畫,於是每個季節的美好都留存了下來。有趣的是,如果把這本書在桌上攤開九十度豎起來, 封面和封底會圍出一塊空間,那麼,書裡的世界也就延伸到現實世界來了。
《照過來照過去》這本書裡的背景是黑色,博伊德用灰色的線條勾勒動植物的輪廓,再用不透明水彩畫出有光線的白色區域,和動植物美麗的顏色。除了描繪小男孩夜間的探索之旅,博伊德也運用了挖洞手法增加趣味,由於頁面是黑色的,小小的洞口不容易被發現,這是她刻意設計的。
故事一開始,從帳篷裡走出來的小男孩拿著手電筒,隨著手電筒照亮的有限區域,看見了黑漆漆的森林裡隱藏的各種動物,讀者也隨著男孩一起夜遊,分享他發現的樂趣。半途,小男孩跌了一跤,手電筒掉了,被小動物撿起來,牠們反過來照亮小男孩和其他動物, 使大家都現身了,最後,所有的動物一起護送男孩回帳篷,小老鼠還留下來,舉著手電筒為小男孩照亮他讀的書呢!而讀者一方面跟隨男孩的腳步前進,一方面可以自己探索,因為透過頁面上設計的小洞,看得到移動的月光,以及更多藏在黑暗中的小動物和開花的植物。如果前後反覆翻閱,還會發現之間的變化與關連。
閱讀無字書的經驗也就是一趟探索之旅,精心設計的無字書必定會在圖畫上和版面上埋下許多線索,讀者只要有耐心地反覆觀看,必定能夠掌握全局,讀出書裡的樂趣與深意。而孩子和大人一起欣賞、共讀,自然而然的培養了閱讀圖畫的能力,和用口語表達描述的技巧。從觀察到描述,進而詮釋的過程,為孩子往後觀賞、思考和評斷視覺藝術,包括廣告、繪畫、攝影、動畫或是電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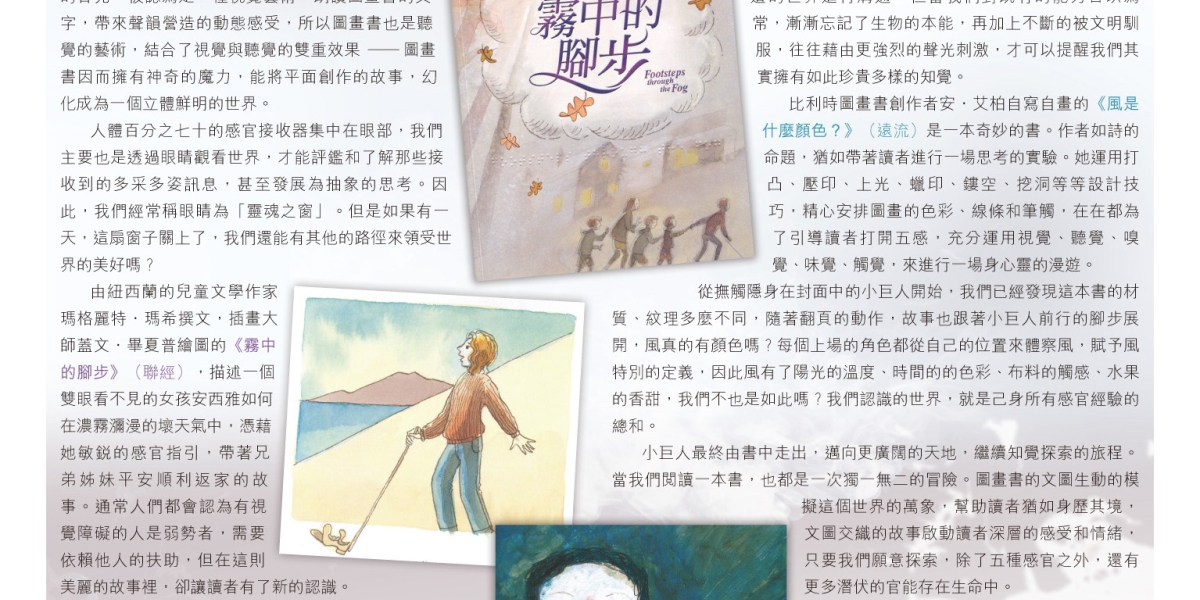

童書的旋律
2016.01.16
跨越邊界,用心看世界
圖畫書因為有豐富的圖像,立刻吸引讀者關注的目光,被認為是一種視覺藝術;朗讀圖畫書的文字,帶來聲韻營造的動態感受,所以圖畫書也是聽覺的藝術,結合了視覺與聽覺的雙重效果 —— 圖畫書因而擁有神奇的魔力,能將平面創作的故事,幻化成為一個立體鮮明的世界。
人體百分之七十的感官接收器集中在眼部,我們主要也是透過眼睛觀看世界,才能評鑑和了解那些接收到的多采多姿訊息,甚至發展為抽象的思考。因此,我們經常稱眼睛為「靈魂之窗」。但是如果有一天,這扇窗子關上了,我們還能有其他的路徑來領受世界的美好嗎?
由紐西蘭的兒童文學作家瑪格麗特.瑪希撰文,插畫大師蓋文.畢夏普繪圖的《霧中的腳步》(聯經),描述一個雙眼看不見的女孩安西雅如何在濃霧瀰漫的壞天氣中,憑藉她敏銳的感官指引,帶著兄弟姊妹平安順利返家的故事。通常人們都會認為有視覺障礙的人是弱勢者,需要依賴他人的扶助,但在這則美麗的故事裡,卻讓讀者有了新的認識。
當其他人平日仰賴的視覺不再管用,安西雅用甚麼來為大家導航?她能聽見樹對彼此輕聲的說著秘密,海浪的聲音就像是白晝緩慢的心跳聲,還有小溪嘩啦嘩啦地翻滾著;她聞到海水的鹹味和海草的氣味,鄰居晚餐和烘培店的香味,薰衣草的樹籬和玫瑰的芬芳,溫度、濕氣、風向⋯⋯安西雅打開全部知覺的雷達,收集來自環境所有的回響,她說:「視覺只是其中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
伴隨著我們賴以維生的呼吸吐納,嗅覺幾乎與我們如影隨形,深藏著歲月累積的記憶;通過味蕾的傳達,味覺混揉了複雜多樣的情緒;觸覺則像一個傳送密碼的使者, 不斷回饋環境的訊息;我們也仰賴聲音表達自己,和周遭的世界進行溝通。但當我們對既有的能力習以為常,漸漸忘記了生物的本能,再加上不斷的被文明馴服,往往藉由更強烈的聲光刺激,才可以提醒我們其實擁有如此珍貴多樣的知覺。
比利時圖畫書創作者安.艾柏自寫自畫的《風是什麼顏色?》(遠流)是一本奇妙的書。作者如詩的命題,猶如帶著讀者進行一場思考的實驗。她運用打凸、壓印、上光、蠟印、鏤空、挖洞等等設計技巧,精心安排圖畫的色彩、線條和筆觸,在在都為了引導讀者打開五感,充分運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來進行一場身心靈的漫遊。
從撫觸隱身在封面中的小巨人開始,我們已經發現這本書的材質、紋理多麼不同,隨著翻頁的動作,故事也跟著小巨人前行的腳步展開,風真的有顏色嗎?每個上場的角色都從自己的位置來體察風,賦予風特別的定義,因此風有了陽光的溫度、時間的的色彩、布料的觸感、水果的香甜,我們不也是如此嗎?我們認識的世界,就是己身所有感官經驗的總和。
小巨人最終由書中走出,邁向更廣闊的天地,繼續知覺探索的旅程。當我們閱讀一本書,也都是一次獨一無二的冒險。圖畫書的文圖生動的模擬這個世界的萬象,幫助讀者猶如身歷其境, 文圖交織的故事啟動讀者深層的感受和情緒, 只要我們願意探索,除了五種感官之外,還有更多潛伏的官能存在生命中。
聖修伯里在他的作品《小王子》中說: 「人只有用自己的心才能看清事物,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對自己、對世界,我們還有太多未知的事物有待學習,雖然心理、生理、文化⋯⋯各種因素都有可能劃下隱藏的界線,阻擋我們邁過障礙,但只要願意用「心」貼近真實世界,就可以有機會跳脫「盲人摸象」的自我中心盲點,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生命不同的價值。多元閱讀是我們打破成見、跨越邊界的出發點。


